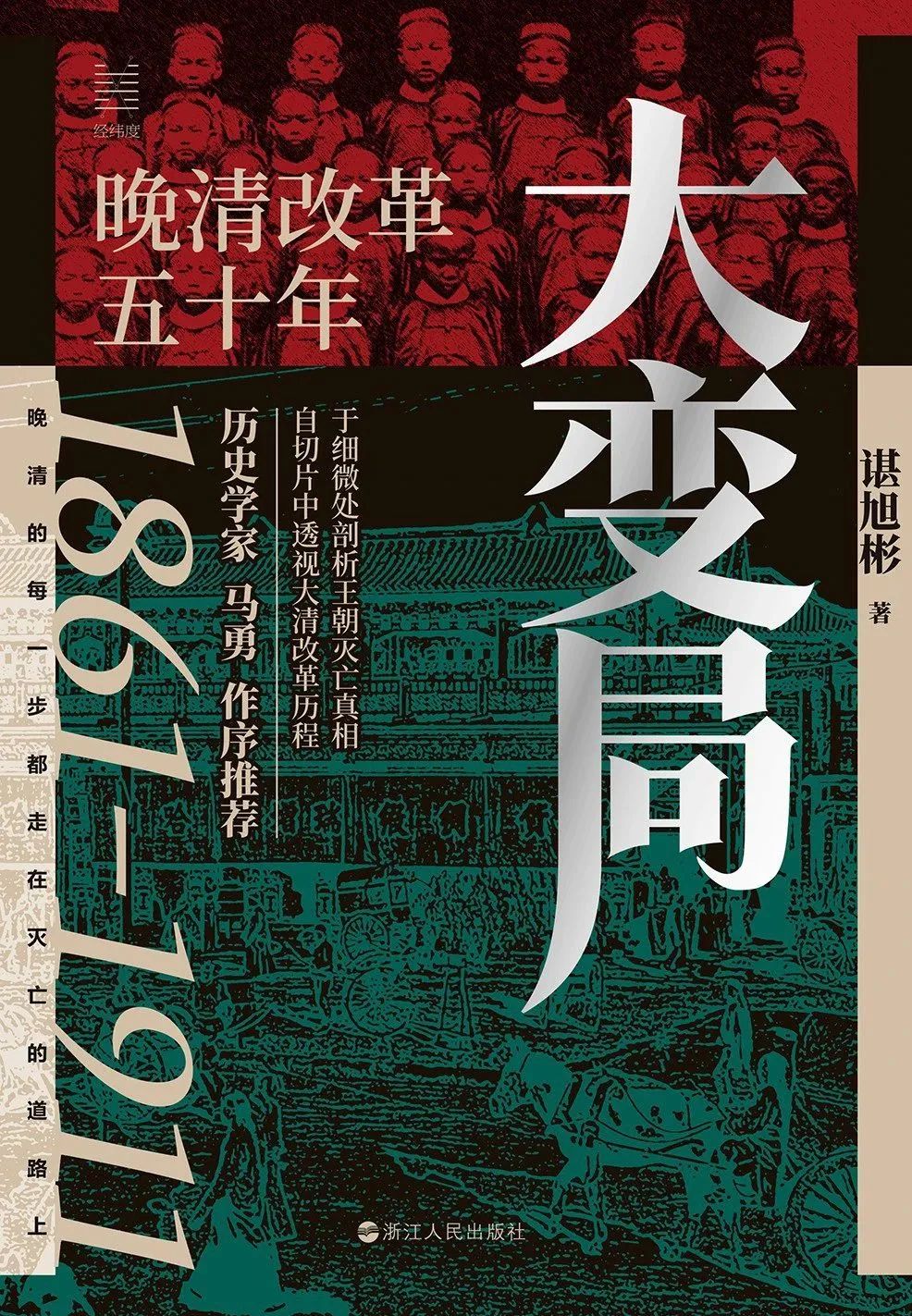
这本《晚清改革五十年》能够正式出版,殊为不易。认真说起来,本书的写作其实始于2010年4月的一个下午。在苏州街的银科大厦,一位媒体前辈问前去毛遂自荐做历史频道的我:你认为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回应说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搞历史者别的做不了,疑今察古鉴往知来总是可以做的。这批旨在总结晚清改革教训的稿子,便是从彼时开始撰写。当年对未来的乐观而今看来已是笑谈,当年对晚清改革的理解,也随着阅读渐广、年岁渐长及现实的反复教育而有了许多变化。最终结集而成的,便是这部超过了五十万字的《晚清改革五十年》。
下文是本书的前言《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一
本书的主题,是晚清的改革与转型。具体而言,是咸丰十一年到宣统三年的改革往事。
之所以不从道光二十年(1840)谈起,是因为该年的英军叩关虽一向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场战争并未将清帝国从旧梦中唤醒。战争期间,沿海地区的士绅多只将英军视为明代的倭寇之流,甚至觉得他们连倭寇还不如。“广东义民”们张贴的宣传资料痛斥英军“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说他们只是一群不懂忠孝节义与礼义廉耻的未开化的畜生,说他们穿的“大呢羽毛”缺了清帝国的湖丝就无法织造,说他们用的“花边鬼银”缺了清帝国的纹银白铅就无法铸成,说他们离不了天朝的茶叶、大黄与各样药材,这些“皆尔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
战争结束后,沿海地区最了解“夷情”的知识分子,也鲜少有人觉得清帝国需要参照外部环境实施改革。梁廷枏是广东顺德人,一向留心“夷务”,做过林则徐的幕僚,是道光二十年英军叩关的亲历者。可即便是梁廷枏这样的人物,在战后总结教训时,仍坚持认为道光时代乃“天朝全盛之日”,断无向洋人学习之理,否则太失体统。梁深信洋人的火炮源自明朝时中国的“地雷飞炮”之术;洋人的舰船“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来自郑和下西洋赠送给他们的图纸;连洋人的数学造诣“亦得诸中国”。只要实事求是将祖宗们留下来的技术与学问参透,“夷将如我何?”洋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2]沿海地区的士绅和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正的惊雷出现在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
这年的旧历八月二十九日,清帝国的大小京官们痛苦地亲眼目睹了北京城落入英法联军之手。一位自号“赘漫野叟”的京官说,洋兵是从安定门入城的,他们登上城墙后便将清军尽数驱离,升起五颜六色的旗帜,还将清军配置在城头的大炮全部掀翻扔进沟里,安上他们自己带来的炮。炮口一致向南,破天荒地对着紫禁城。[3]时任礼部精膳司郎中的刘毓楠,也记载下了相同的一幕。他在日记中说,洋兵进城是在二十九日的中午时分,大概有五六百人,进城时“我兵跪迎,观者如市”——或许是觉得保留这段史实不妥,他写下这八个字后又将之点掉了。洋兵在安定门城头五虎杆[4]下安置了一尊大炮,在东边城墙上安置了四尊小炮,在城楼下方居中之处安置了两尊大炮,炮口全部朝南指向紫禁城。[5]
数天后,九月五日,留在京城负责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䜣惊见“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探听后得知是洋兵正在焚烧圆明园与三山等处宫殿。他后来告诉已远遁至承德的咸丰皇帝,说自己登高瞭望之时火光犹未熄灭,“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6]同一天,三十岁的江西士子、会试落榜者陈宝箴也见到了圆明园的冲天火焰,他“登酒楼望之,抚膺大痛”[7]。
咸丰十年,按干支纪年是庚申年。故以上种种,皇帝出逃、京城沦陷,圆明园宫殿被焚,在清代人的历史记忆里被称作“庚申之变”——不但士大夫们在私人著述里这样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官方档案也普遍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无人将道光二十年(按干支纪年为庚子年)的英军叩关称作“庚子之变”。魏源有一本记载英军叩关始末的著作,初名《夷艘寇海记》,后更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二字是清帝国传统华夷秩序下的常见词汇,意味着事情仍在清帝国的控制范围之内,至少清廷朝野自己如此认为。庚申之变则不然。京城沦陷宫殿被焚,是清军入关建政二百余年来前所未有之事,不独咸丰皇帝心胆俱裂仓皇逃亡,朝野士大夫也普遍心痛欲碎。朝野广泛使用“庚申之变”这个词,意味着庙堂与江湖皆不得不承认维持传统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不得不容忍一种不受欢迎而又无力抗拒的新秩序出现在清帝国。
晚清的近代化改革,便是在这种心胆俱裂与心痛欲碎中启动的。

二
本书采用了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
所谓半编年半专题,指的是书中内容虽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来排布,但并未将所有事件皆罗列其中,而是自每一年中选出一项与改革关系最为密切的事件,围绕该事件做集中论述。自1861年算起,至1911年清廷灭亡,晚清改革持续了五十一年,书中共论述了五十一桩与改革有关的事件。这样做的好处是,纵向上可以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改革演化脉络;横向上方便观察每一桩具体改革事件的缘起与成败;整体上有助于回应这样一个问题:这场绵延了半个世纪的改革,其终点为什么会是辛亥革命?
按笔者的理解,晚清改革的终点之所以是辛亥革命,是因为这五十年的改革并不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而是一条倒U型曲线。其分水岭,也就是倒U型曲线的顶点,是1884年的甲申易枢。曲线的前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艰难突破种种阻碍向前;曲线的后半段,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减速放缓,最后走向了反改革。改革趋势的这种变化,具体体现为改革主持者与参与者、改革阻力、改革目的与改革对象的变化。
在甲申易枢之前,改革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具体的推动者是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地方督抚,以及部分正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体制中人根深蒂固的愚昧,这也是改革推进速度缓慢的主因。
改革的短期目的,是扭转咸丰皇帝的施政路线,重新团结官僚集团以重塑政权向心力,并缓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便腾出手来彻底镇压太平天国——庚申之变前,咸丰皇帝自命雄才,大量起用酷吏与主战派人士,对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皆持高压与强硬立场。咸丰皇帝死后,清帝国进入由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同治”的新时代,随即对内取消了高压反腐,对外变主战立场为主和立场。改革的长期目的,则是引进列强的先进技术,包括征税技术和军事技术,来提升清帝国的实力,尤其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以达成抗衡列强乃至制服列强的目的。当时流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8]之说,本身便清晰点明了这场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制服嚣张的夷人、重塑天朝的荣光。
为达成该目的,外交系统、军事系统、税赋系统和教育系统,皆是主要的改革对象。外交系统由理藩院转型为总理衙门,正式与近代条约外交制度对接,并向外派驻了使节。军事系统大量换用洋枪洋炮,致力于建设自己的近代化兵工厂,并采购洋船组建了近代海军。税赋系统主要是引进了近代关税制度,并开征厘税大搞鸦片财政,让清帝国的税收蛋糕有了大规模增长。教育系统的主要培养对象是外语翻译人才、能够操作近代机器的人才、能驾驶近代军舰的人才。在甲申易枢之前,大部分的改革派人士,上至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中至洋务派地方督抚,下至民间开明派知识分子,都支持上述改革目标和改革手段。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被清帝国朝野上下视为检验洋务自强改革成效的一场“大考”。上至慈禧太后,中至内外群臣,下至民间士绅,皆认为清帝国在经历了二十余年洋务自强改革之后,当有足够的能力与法国军队一战,保住越南这个藩属国,当有足够的能力让庚申之变的耻辱不会再重演。于是,在这场“大考”中,地方督抚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李鸿章遭到了慈禧太后的严责,朝廷中对战事持保守立场的恭亲王奕䜣和总理衙门众大臣更是被集体逐出了决策中枢。此战最后以战场上互有胜负,和约里没有赔款,甚至还以“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9]这种文字游戏宣布保藩成功的方式结束。这种结束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清帝国朝野对二十年洋务自强改革的期望,让他们觉得清帝国确实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任凭数千洋兵纵横驰骋的弱者——至少慈禧太后本人是这样认为的。
甲申易枢之后,王与后“同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恭亲王奕䜣被逐出中枢,不了解改革真实含金量的慈禧太后成了唯一的强力决策者。太后安坐深宫,既无法像前线将领那般直观感受到清军与法军在海、陆两线上的巨大差距,也无从体察法国愿意签订不赔款不割地和约的真实逻辑。朝野内外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于是,中法战争后的清帝国上下普遍笼罩在了一种虚骄的氛围之下,之前的洋务自强改革不但没有继续深化至体制层面,反而开始减速。能直观体现这种虚骄心态与改革减速的一项史实就是:在中法战争结束的同年,洋务改革的主持者慈禧太后便不惜耗费巨资,开启了三海重修工程[10]。太后觉得中兴已大体完成,享乐的时刻已经到来。
改革减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外交方面,总理衙门从改革的重心所在,沦为了疲于奔命的中外冲突救火员,知己知彼融入国际社会成了空谈。军事方面,陆军的近代化改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几乎停止,北洋海军也受限于经费,只能以残阵宣布成军。军事体制层面的变革(比如成立独立的海军部)更是无从谈起。经济领域的改革则止步于官督商办,曾经的明星企业轮船招商局由兴盛急骤转向衰落,中枢全力扶植创办的汉阳铁厂也长期炼不出一根合格的钢轨。教育改革更是毫无动静。当改革已然减速,虚骄却日甚一日时,悲剧很快就发生了。1895年的甲午战争不过是悲剧的开幕,1900年的庚子之变才是悲剧的高潮——晚清改革始于庚申之变京城失陷皇帝外逃的奇耻大辱,最后又回到庚子之变的京城失陷太后携皇帝外逃。历史转了一个四十年的大圈,又回到了起点。
在这个改革减速的过程中,改革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不断发生着分化重组。许多以前反对过“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在经历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器械的积极分子。许多以前只主张“师夷长技”的朝野士绅,也在经历了各种现实教训后,变成了呼吁实施制度改革、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的积极分子。
这场分化重组,扼要而言如下:1890年代以前,改革派们全部团结在朝廷周围,支持朝廷搞洋务自强,不存在立宪派,也没有革命党,几乎无人主张变君权时代为民权时代。甲午年之后,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零星出现,但均未成型,能将自强改革与民权转型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有限。此一时期,大多数改革派仍与朝廷紧密团结在一起。1900年慈禧太后的荒唐决策给国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骤发展,立宪派也音量大增,开始在朝野不断发出向民权时代转型的呼吁。日俄战争后,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以各种“议会不得干预”为主要内容的《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后,许多立宪派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了。
这当中,最巨大的变化是原本身为改革主持者的慈禧太后,逐渐成了改革的阻力,成了亟需改革掉的对象。
1880年代之后的各种现实教训,让改革者们渐渐意识到,“船坚炮利”固然是重要的改革目标,合理的中枢决策机制同样必不可少。技术与装备再先进,置身于僵化乃至异化的体制中也是无法发挥效用的。中法战争期间,中枢的朝令夕改与不负责任已让身在前线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颇为不满,促使他于临终之际上遗折呼吁朝廷开设“议会”[11]作为新的中枢决策机构,以避免中枢决策沦为权斗的工具。甲午年的惨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中枢决策机制有问题,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人的权斗影响太深。而最让体制内改革派痛心者,莫过于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对世界宣战,再次酿成京城沦陷的苦果,《辛丑条约》中还出现了天文数字般的赔款额度。这一惨痛结局让许多体制内官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再次痛感中枢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两广总督陶模在庚子之变后上奏,明确请求开设议院,提出“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的构想,便是希望以“议院”这个新机构为新的决策中枢,来取代慈禧太后的独断。[12]
再往后,慈禧太后启动所谓的“清末新政”,追求以《钦定宪法大纲》来收回地方督抚手中的财权、人事权和兵权,以重塑皇权的无远弗届和至高无上;地方改革派督抚和民间改革派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等措施,让国家转型进入民权时代,让自己的权利获得制度上的保障。拒绝让清帝国进入民权时代的慈禧太后和她的继承人,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改革的反对者,成了被改革的对象。
这条倒U型改革曲线,正是晚清五十年改革最后以辛亥革命收场的主因。半编年半专题的写作形式,当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这条悲剧性的曲线。

三
最后分享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生出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愚民教育虽然有助于维持统治,但在变革时代,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康熙皇帝当年亲自下场论证“西学源于中学”,且胁迫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集体参与论证,导致后世许多清代知识分子信以为真视为真理。当恭亲王奕䜣决定向洋人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时,这些被漫长的愚民教育桎梏了见识与逻辑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便纷纷跳了出来,有人抬棺死谏,有人正面互怼,让亲眼见识过洋人坚船利炮的恭亲王不胜其烦又无可奈何。庙堂之上这类人很多,导致许多改革无法由总理衙门这个中枢机构直接推行,只能仰仗曾国藩与李鸿章这些地方督抚先将生米(改革)煮成熟饭。江湖之中这类人也很多,导致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却拿他们毫无办法,只能对领头者施以“被精神病”的处置。
第二点感想是不但要开眼看世界,还得正眼看世界。开眼看世界很容易,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世界的互相连接,想要关上大门闭上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晚清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开眼看世界的人虽然很多,正眼看世界的人却太少,而且但凡有人正眼看世界,便会遭到知识圈与文化圈的集体排斥和攻击。徐继畬的命运如此,郭嵩焘的命运也如此。正因为整个社会敢于正眼看世界的人太少,敢于将正眼看世界的感受诚实说出来的人太少,才会发生冯桂芬将改革主张深埋起来的事情,才会出现刘锡鸿这种内心认知与公开发言完全相悖的两面人,才会有报纸媒体为了取媚用户不惜扭曲甲午战争的胜负真相,将清军描述成战无不胜之师。
第三点感想是晚清的五十年改革中,与列强对抗的心态太重,与文明拥抱的心态太少。诚然,这场改革本身就是外部环境刺激的结果,危机感是晚清改革最核心的驱动力。没有庚申之变,就没有洋务自强改革;没有天津教案和马嘉理案,清廷也未必会在1876年对外派驻公使;没有《里瓦几亚条约》事件,清廷也未必会允许李鸿章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外部环境的刺激,必然引起清廷对列强的不满,必然让清廷中枢生出“雪耻”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就一场改革而言,其终极目的绝不应该只是为了“雪耻”,绝不应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对抗,还应该有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拥抱那些先进的技术文明,拥抱那些合理的制度文明,将之纳为己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晚清漫长的五十年改革中,在清廷中枢里几乎见不到这种意识。1884年之前,每一次关于改革问题的高层集体讨论,无论是恭亲王的奏折,还是慈禧太后的懿旨,抑或是地方督抚的呈文,总是以洗雪庚申之变的耻辱为改革的终极目标,拥抱先进的技术文明(如枪炮轮船)与制度文明(如近代化公司),反退化成了实现雪耻这一目标的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最终发展成了1900年的“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13]。
五十年改革史中能生发感想的细节很多,远不止此。如满洲本位意识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阴魂不散;如转型时代对掌舵者见识的要求其实远远大过权术;如坐而论道的批评者一旦直接参与改革事务很快便会转变立场,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言。
对过去展开反思,往往源于对未来有所期许;追问“我们从何处来”,其实是为了回答“我们向何处去”。希望本书在这方面,能够为有所关心的朋友稍稍提供一点助益。
—END—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